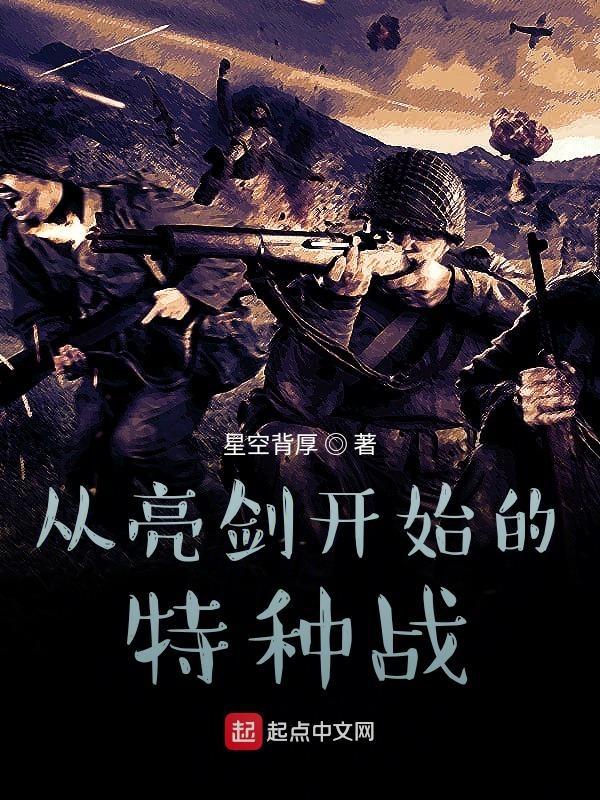鹅绒锁>小病秧子养护指南 > 3040(第13页)
3040(第13页)
之后医生把盛恪喊了进去,和盛恪说了一下傅渊逸的情况,“主要还是由于车祸造成的慢性型创伤后应激障碍。”
他这种情况,一方面是由当时身体重伤造成的,另一方面是由失去至亲造成的。傅渊逸常做噩梦也是创伤再体验的一种表现,并且伴有一些躯体化反应。
幸运的是,陈思凌在最一开始就有意识地让傅渊逸进行过一段时间的心理治疗,没让他的问题过度恶化。
“小逸对感情需求很高,对人际关系过度依赖,都是源自于安全感的缺失,他对分离、分别、死亡的恐惧感很深。作为他的家里人,还是希望你们能多陪伴他,这样的话,也会对他的心理治疗有所帮助。”
傅渊逸从诊室出来后,没怎么说过话,牢牢牵着盛恪不肯撒手。
跟走丢过的小狗似的,好不容易回到主人身边,要前前后后黏着、看着才能安心。
傅渊逸也一样,好似那分开的三小时,让他患上了分离焦虑。
情绪也很低落。
盛恪心疼。不知道怎么哄,只喊着他的名字,“傅渊逸……”
傅渊逸抬了点头,鼻尖无意蹭过他的脖子,“咋又叫全名了……”他说得轻,听着有点委屈。
盛恪喉结滚了滚,喊了声逸宝。
“很难受?”他问。
傅渊逸回答:“不难受。但是哥……我有点累。”
盛恪的手抚过他的额,停住,俯身吻在自己手背上,“要不要睡一会儿?”
“哥,还有糖吗?”
盛恪从口袋里摸了一颗,拆了包装喂给他。
傅渊逸含着糖,靠着盛恪一路睡到家,到家后喝了口水,又蜷进房里去睡。
如同某种冬眠的动物,用睡眠来抵御严寒,度过危险。
盛恪什么也没干,傅渊逸睡觉,他就在旁陪着。
阳光漫过纱帘,从金色变成橘色,最后太阳西沉,夜幕升起。
盛恪看到了时间从傅渊逸身上缓缓流淌而过。
然后呢?
时间走了,留下了依旧痛苦的傅渊逸。
它带不走任何,也治愈不了任何。
傅渊逸的伤口结了厚重的痂,一层又一层,一年又一年。
结痂之下,依然溃烂生疮-
傅渊逸委顿了一天,隔天看上去就好了许多,恢复了元气。
然后,他哥便去他二爹的公司实习了,甚至没点缓冲!
傅渊逸一早醒来,脑子还钝呢,听闻这样的噩耗,卷毛都耷拉了。
“哥,你今天就去了?不多陪我一天?”
盛恪系着纽扣,回了个淡淡的“嗯。”
傅渊逸彻底枯萎了,在床上抱着被子问,“那我咋办?”
盛恪看他一眼,“在家待着。”
傅渊逸脑袋创进被子里,闷声说,“全家我最笨,我最弱,现在我还最闲最废物了哇……”
盛恪过去,在被子团上轻轻拍了两下,“那你问问凌叔,问他能不能让我把你也稍上。”
傅渊逸钻出来,才闷了几秒就有点喘了,“真的?”
“嗯。带上你的暑假作业。”
“……”傅渊逸的天又塌一回。
最后他没跟着盛恪去,他完全不想在陈思凌的总裁办公室里丢脸地做他的高一暑假作业!
去是没跟着去,但心没少操。